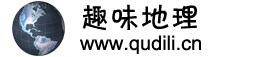作者:佚名 来源于:世界儿童文学网
是的,红菱艳故事的隐喻是实现自我价值。
前言
《红菱艳》于1948年首映,通过“戏中戏”的方式,将安徒生小说《红舞鞋》融入真实世界,使其在真实世界的层次上与故事的层次同构,在戏剧内外的层次上形成一个高度统一的形象。
从而在两种层次的交迭中获得叙述的均衡,从而使作品在这种同构嵌套的形式下,呈现出一种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不朽之美。
迈克尔·鲍威尔的《红菱艳》,这一影片在1948年赢得了第二十一届奥斯卡的诸多大奖,并一度被视为美国历史上最好的音乐影片。

作品完美地将舞蹈语言与电影语言融合在了一起,并将其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也就是“戏中戏”与主体情节相结合,构成了一种典型的嵌套结构。
内部叙述是以安徒生《红舞鞋》为原型的芭蕾舞,外部叙述也是以一种悲剧性的方式来叙述一个人一生都沉浸在对艺术的迷恋中,最终陷入了疯狂。
戏剧性的情感节拍被“揉”进了当代的小说里,使得它对经典的模拟和重现,“戏中戏”的双重意义拓展了该小说的内在意义。
文章以《红菱艳》为个案,对“剧”中“剧”的“嵌套”进行了解读,探讨了“剧”中“嵌套”的艺术意义和产生机理。

《红菱艳》与安徒生的神话
《红菱艳》的内在叙述采用了安徒生的《红舞鞋》的芭蕾方式,讲述了一个名叫珈伦的孤儿,她被一位好心的母亲收养,看到橱窗里堆积如山的鞋子,她很眼馋,于是一个年轻的鞋匠把一双用魔法制作出来的红色舞鞋递给了她。
她没有做任何祈祷,她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鞋子上。
虽然母亲病入膏肓,但她还是穿着红色的舞鞋去了舞会,她的表演让所有人都为之惊叹,但舞会结束后,她才知道自己的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了,只能一个人在荒野和坟墓中跳舞。

当她的母亲在没有人照顾的情况下死了的时候,珈伦仍在跳舞,她恳请小鞋匠把她的脚从她的脚上割下来,最后,停止了舞蹈,珈伦也死了。
舞蹈演员维多利亚•佩奇被剧中的角色所迷住,开始讲述真实的故事:剧院的导演莱蒙托夫支持蓓姬出演《红舞鞋》。
在她事业的巅峰时期,她爱上了一位著名的音乐制作人克拉斯特,但他们却因为违反了该团体的禁令而被赶出了舞台。
蓓姬离开了这个世界,她无法掩饰自己的失望,她想要重新回到《红舞鞋》中,但她的丈夫强迫她放弃了这个角色,在莱蒙托夫的极力劝说下,蓓姬伤心欲绝,想要追上离开的丈夫,但最终还是死在了马车上。

这两个故事,都围绕着可怕的“红舞鞋”而进行,这是一种对亵渎和虚荣心的人的惩罚,但在传播过程中,却发生了变化,变成了一种典型的形象,而这种形象,就像是一种神奇的符号,让人欲罢不能。
两种叙述层次的交迭
在影片《红菱艳》中,安徒生的神话是其真实故事的母体,具有一定的象征性,在叙述层次上的神话剧情在许多情况下都曾进行过多次的插足,并将其提升到了更高的境界。
在一个童话舞剧中,那个耗尽了少女所有生命的红舞鞋就是现实层面上蓓姬的生活写照,这两个叙述层次互相交织,互相映射,实现了完美的对接。
对亵渎上帝的处罚,神话故事的主要冲突是:宗教与物质的冲突。

影片的主要冲突在于“文艺”和“爱”的对立面,莱蒙托夫把文艺看作是“宗教”和“少女”应当崇拜的“神”;克拉斯特的“爱”使她的“专注”产生了偏离。
这就像她的“虚荣”和她的“专注”一样,“爱”的二元性就像“信念”和“虚荣”的二元性一样,存在矛盾。
美国学者彼·弗雷泽认为,“在《红菱艳》中,通过将两种矛盾的因素融合在一起,从而产生了一种失衡,这就是《红舞鞋》的主旨所在。”
最终,这两种叙述层次均因前者(物质欲望,爱情)对后者(信仰,艺术)的践踏而得以完成。
有些人认为这是一场体育,一首诗歌,一种情绪的发泄,但在莱蒙托夫看来,这是一种信念。

蓓姬应莱蒙托夫的邀请,在地中海的一处隐蔽的花园里,她正在排练《红舞鞋》,穿着华丽的礼服,唱着威尔第的歌曲,登上了一条通往王宫的阶梯,这是蓓姬生命中最美好的一章。
在《爱情一条》中,莱蒙托夫让蓓姬完全沉浸在《红舞鞋》的旋律中,让克拉斯特陪着蓓姬一起用餐,当他演奏出一首童话故事中的舞蹈时。
克拉斯特阐释道:“当你的舞伴将你高高举起,你就会变成一朵鲜花,一朵白云,一只鸟儿,听过这首歌的人,就会有一种置身于舞蹈之中的错觉。”
就在这里,当珈伦在大厅中间,穿着红色的鞋子跳舞时,她的自尊心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在舞曲的开头,有一个和她一起跳舞的恋人,但是她被红舞鞋的魔法从她身上驱赶了出去,那个恋人重新出现在她面前,变成了一个从她面前掠过的爱情女神,然后变成了一个在丧葬行列中的神父。
在克拉斯特的真实世界里,他同样输给了她,但是他也要赢给他的爱人。
在艺术界,莱蒙托夫给蓓姬穿上了一双红色的舞鞋,让她失去了所有的意义,他对自己的作品提出了苛刻的要求,他相信一个只会沉浸在无味的感情中的人,是不会有出息的。
这是他给蓓姬树立的榜样,也是为了警告她,他将一名刚刚结婚的舞蹈演员赶出了自己的生活。
莱蒙托夫虽然冷漠,但他始终坚持着对艺术的纯粹,就像一个保护神的使者,他坚持着“艺术应该在生命之前”的观点。

就像他说的那样,沉浸在感情里,确实会让舞蹈演员背离自己的艺术信念,比如蓓姬在《天鹅湖》里扮演奥杰塔,在舞台上和王子在湖边告别时,克拉斯特向她投去一个深情的眼神,与舞台上悲伤的场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对艺术的一种侮辱。
此外,剧末克拉斯特竭力阻止蓓姬上台,并在伦敦王室大剧场拒绝了他的演出,并把她的表演抛在脑后,由于她的私人感情,使这场演唱会无法继续下去,她又一次玷污了这场表演。
在神话故事中,珈伦的这种行动与她的思想完全一致,她在接受圣体的时候,她的思想完全被她的红舞鞋所吸引,她甚至忘了自己。
安徒生神话里,一位年迈的老者,手持一根手杖,许下了祝福的诅咒,以自己的虚荣心引诱珈伦去做一双红色的舞鞋。

在真实生活中,克拉斯特用爱的承诺引诱蓓姬离开了美术,两人从相爱到结婚再到私奔,都变成了对美术的一种亵渎,就像对宗教的虚荣心一样,最终与莱蒙托夫的合作者决裂。
克拉斯特曾经说过:“蓓姬将成为他快乐的回忆”,证明了他预见到了最终将他们分开的命运。
在神话故事中,对亵渎上帝的人来说,删去两个足够偿还肉体欲望的罪孽,蓓姬的死亡,就是为了惩罚那些对艺术不敬的人。
无意识的舞蹈
这双红鞋子最大的特点,就是永远不会停止,也就是无法摆脱。

莱蒙托夫和蓓姬初次相遇时所说的那番话,成为了这个故事的一个引子。
“你为何要舞蹈?”莱蒙托夫问道,“你为何要生活?”蓓姬问道。
莱蒙托夫很欣赏这个聪明的回答,但他又不能说出更多的话来,只能说:“我不明白,但我想要活命。”
蓓姬骄傲地说:“我也是这么想的”,该对白一方面说明了“爱舞如命”,另一方面也暗示出莱蒙托夫是被迫生活的,蓓姬是被迫跳舞的。
因此与神话故事里的珈伦是“一踏上红舞鞋,就永远也跳不完”的,其共同特点是“被动”,受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控制,这种力量来源于一双红舞鞋。

蒙特卡罗的首部演出《红舞鞋》,是蓓姬演艺事业的开篇,她穿着一袭轻盈的长裙,踏着轻盈的步伐,宛如仙女下凡,舞蹈家的金红长发,与她那一双闪闪发光的红舞鞋交相辉映。
莱蒙托夫大喜道:“我想让你成为一名优秀的舞蹈演员,但我想先问你一句,你想要的是什么?”
蓓姬斩钉截铁地说:“跳舞!”莱蒙托夫给她描绘了一幅宏伟的蓝图,“罗马,维也纳,斯皮戈尔摩,美洲,伦敦,《奥菲利亚》,《吉赛尔》,《天鹅湖》,《睡美人》,《仙女们》,《神奇玩具店》,这些都是我们的翻版,让整个世界都认识你,我负责讲话,你只要专心跳就行了。”
横扫全世界的巡回和仙子般的少女们在舞蹈大厅里闪耀着耀眼的光芒,博得大家的称赞,构成了一个共同的构架。

然而,快乐之后,光线黯淡下来,珈伦的舞蹈从活跃变成了消极,从主动变成了被动,她越过了原野和树林,翻越了山谷,淋了一场又一场的大雨,晒了一天又一天的阳光。
晚上跳舞,白天跳舞,直到教堂的坟场;珈伦在她的母亲生病去世后,一直在旷野上翩翩起舞,一直跳到长满尖尖的玫瑰刺破了她的皮肤,最后,她的两条腿都被砍掉了,这是一场诡异而黑暗的舞蹈。
两个故事里的少女在沉浸在自己的执念中时,都会被这一幕所牵制,明明知道自己被控制了,但却无法抗拒,只能陷入绝望。
在现实世界里,蓓姬因为爱而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她尝试着摆脱自己的红舞鞋,

但在自己的婚姻里,她很难实现自己的价值,半夜起来,她会从箱子里掏出自己的红舞鞋,握在手心里。
因为爱,她不能再跳舞了,没有了舞蹈,就像是没有了自己的信念,蓓姬无法继续自己的人生,内心充满了痛苦。
莱蒙托夫每天都在想着怎么才能赢得她的心,当他们又见面的时候,老头儿对他说:“自从你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人给你表演《红舞鞋》了,以后也不会再有了。
把这双红色的鞋子穿上吧!蓓姬,请你再次为我们起舞!”
蓓姬被艳丽的红色舞鞋所迷住,想要重拾成名,但她的丈夫强烈地拒绝了她,她被各种冲突所迫使,从阳台上一跃而下,成了一辆疾驰而去的列车车轮下的幽灵。

在近代的工业化世界里,列车是一个类似于“红舞鞋”的形象,在影片里也经常被看到:比如,克拉斯特与蓓姬在旅馆的露台上相遇,相爱了,一辆列车从身边经过。
还有蓓姬辞去职务,与莱蒙托夫再次相会时,列车成了他们交谈的主要地点,甚至莱蒙托夫还开玩笑说:“看来我们命中注定会在这个火车站相遇。”
这辆列车的确是一种隐晦的象征,象征着舞蹈演员的宿命,他们会沿着一条固定的轨迹前进,而他们却不能完全掌控自己,就像蓓姬一样,她也会沿着一条固定的轨迹前进,这条轨迹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事先设定好的,就像《红舞鞋》一样。
在这里,有着同样作用的“红色舞鞋”与列车发生碰撞,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情绪冲击,从而印证了“红舞鞋”“非自由”的特性。

用死来做一个均衡
在最后的表演开始之前,克拉斯特赶到了现场,强迫蓓姬退出表演。
当一切冲突都集中在一起的时候,莱蒙托夫抛弃了自己的感情,说出了一句话:“跟着他,你就别想再跳下去了,别想变成一个了不起的舞者,你将会带着一群哭泣的小孩。”
克拉斯特执意要把爱情据为己有,说:“假如你再这样下去,那就是出卖了我们的爱情,破坏了我们的爱情。”
蓓姬心如刀绞,桌子上的克拉斯特与莱蒙托夫的画像嵌在一起,足以说明她对他们的喜爱,对他们的栽培与塑造。
他们之间的争斗,就像《红舞鞋》中的一幕一样,一个黑色的身影张开双臂,将伽伦包裹在其中。

而魔鬼则变成了莱蒙托夫和克拉斯特,少女瞪大了眼睛,一脸恐惧地看着这一幕,似乎在告诉所有人,蓓姬是被这两个人给活活地撕死的,一个是为了艺术,一个是为了爱情。
蓓姬伤心地决定留下来继续扮演《红舞鞋》的角色,她的老公一怒之下离开了她。
莱蒙托夫劝道,“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人生无足轻重,从现在开始,你的注意力,集中在舞蹈上。”
蓓姬泪流满面,蜷曲着身子,在上台之前,她突然想起了自己就是那个珈伦,那个穿着红色舞鞋,走到人生尽头的少女,她在心里大声呐喊着,她不能没有老公,她跑出剧场,想要去追逐自己的老公。
但那双红色的舞鞋却不听使唤,她像是一个疯狂的芭蕾舞演员,根本停不住脚步,从阳台上一跃而下,被一辆疾驰而过的列车狠狠地砸在脸上。

满身是血的蓓姬依偎在自己的丈夫的臂弯里,临终前说了一声:“朱利安,替我把红舞鞋脱掉。”
克拉斯特帮 蓓姬慢慢地把鞋子脱掉,就像是一部芭蕾的结局中,神父拥抱着已经死亡的珈伦,为她脱掉了红舞鞋。
蓓姬在戏剧层次上的介入,在真实层次上用“死”的方式重现“戏中之戏”。
在莱蒙托夫的死中,他对所有的人都说:“蓓姬已经不在了,但我们还是要继续上演她的戏剧,《红舞鞋》是她的成功;《红舞鞋》这部电影也是由她完成的,我们相信,死者的灵魂也会这样想的。”

一盏探照灯,跟随着“蓓姬”的身影,她的生活,她的舞蹈,她的故事,她的人生,她的舞步,她的结局,她的起点,她的终点,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循环。
所以,在这样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结果中,有一种奇怪的均衡。
蓓姬遵从莱蒙托夫的要求,把她真实的生活融入到她的作品中去,使她的作品获得最纯净、最崇高的感受,从而使她在现实和戏剧两个层次上取得交集。
弗雷泽在评价影片时说:“无论是芭蕾还是电影,对于真实的叙述都是以主人公的死而结束的。

因此,在两种不同的叙述层次上,都存在着一种不均衡,但是,这种不均衡导致了两种不同层次上的矛盾,而这种矛盾正是由“红舞鞋”这个形象所引发的。
结语
《红舞鞋》向真实的生活展现,蓓姬将自己完全融入到了真实的生活中,成为了真实生活的一部分,
因此,古典的故事被同构地嵌入到了当代的历史事件中,呈现出了一种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艺术魅力。

就像伽达默尔所说的那样:“对艺术的真实的描述,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美学,而是一种对真实的认识和揭示,一种对过去和现在的认识。”
“红舞鞋的形象,是古典小说和真实小说共同创造出来的审美元素,它所蕴含的特殊意义,不再只是一种文字,而是一种玄之又玄的本质,它那永不改变的意和味道,更加突出了生命的无穷无尽的悲惨宿命。”
在影片的开头和结尾,都有一句台词:“致敬安徒生童话《红舞鞋》。”
上一篇: 颜料用什么东西可以清洗掉(颜料弄到衣服上怎么去除)
下一篇: 打气筒打真空胎技巧电动车(打气筒打真空胎打不进去气)
【相关文章】
版权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观点,作为参考,不代表本站观点。部分文章来源于网络,如果网站中图片和文字侵犯了您的版权,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处理!转载本站内容,请注明转载网址、作者和出处,避免无谓的侵权纠纷。